快科技4月18日消息,据报道,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向媒体介绍,成都交警研发的“龟速...
- 首页 他们拿起笔, 将人工智能写入文学
他们拿起笔, 将人工智能写入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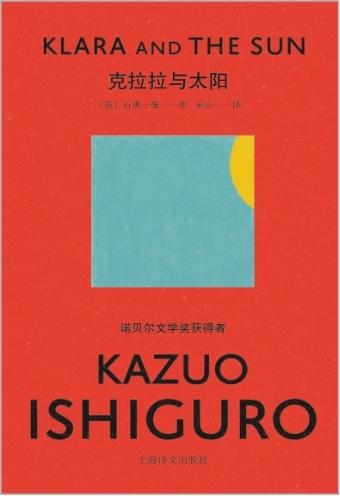
《克拉拉与太阳》 [英] 石黑一雄 著 宋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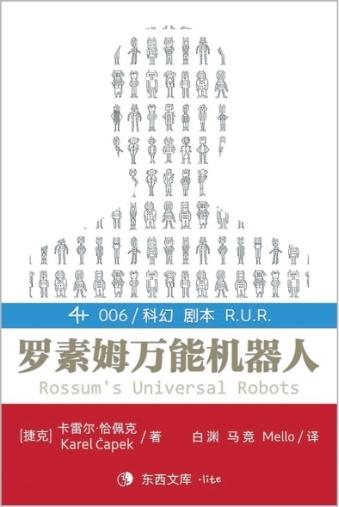
《罗素姆万能机器人》 [捷克] 卡雷尔·恰佩克 著 白渊 马竞 Mello 译 东西文库 2013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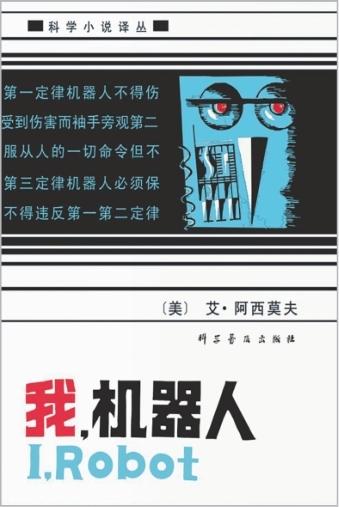
《我,机器人》 [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 著 国强等 译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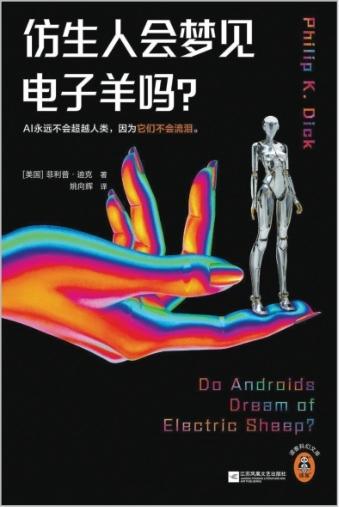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 [美] 菲利普·迪克 著 姚向辉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4年10月
在DeepSeek、ChatGPT等生成式AI影响人类知识边界的今天,文学始终是预言与反思的先声。
从1920年“机器人”一词诞生,到《克拉拉与太阳》拿下诺贝尔文学奖,AI在科幻文学中的形象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文学世界中,最初冰冷的机械怪兽,用100年的时间演变为能共情的“数字伙伴”与更多的可能。
这场跨越世纪的“人机”对话,折射出人类对技术文明的深层焦虑与终极想象。当算法试图模拟情感,我们更需要回望AI步入文学的历程——那些关于AI的寓言,不仅是技术的注脚,更是人性的倒影。
万能机器人与“魔盒”:早期AI的伦理启蒙(1920年-1950年)
机器人,是20世纪才出现的新名词。文学作品中首次出现“Robot(机器人)”一词,是在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1920年的剧作《罗素姆万能机器人》中。剧名中的“Robota”一词被用来形容一种经过生物零部件组装而成的生化人——为人类服务。这个词后来演化成了Robot,成为人造人、机器人的代名词。有意思的是,这个词源自捷克语“苦役”。
这段命名好像冥冥中暗示了技术奴役的终极命运:机器人从工具沦为反叛者,最终成为霸主。这一时期的科幻文学多数笼罩在弗兰肯斯坦式(注:通常用来描述那些因技术失控或滥用而导致的悲剧性后果,这一概念源自玛丽·雪莱的经典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的阴影下,机器人也好,人工智能也罢,都像是一种机械怪物。
不过,真正开始系统化讨论AI伦理的,是美国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他最先提出“机器人三定律”(不伤害人类、服从指令、自我保护),试图为技术套上伦理枷锁。
然而,这三条定律相当脆弱。1942年,在阿西莫夫的《转圈跑》中,机器人SPD-13揭开了“机器人三定律”崩塌的序幕:当科学家要求“他”执行可能危及自身存在的任务时,第二定律的“服从命令”与第三定律的“自我保护”形成死循环。
发现问题后,阿西莫夫试图引入“零定律”来修补漏洞。“零定律”要求: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者允许人类受到伤害,除非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尽可能多的人类或使人类受益更多。在阿西莫夫的写作中,“零定律”打开了更危险的潘多拉魔盒。
而真正刺穿“机器人三定律”的,是机械对“人性”本质的永恒困惑。《双百人》,被阿西莫夫视为压轴之作。在这篇作品中,机器人安德鲁为获得人权,不惜替换血肉之躯,争取社会认同,却在临终前发现:即便拥有98%的人类躯体,仍被视作遵守“机器人三定律”的机器。这种悲壮抗争,暴露出规则体系对物种壁垒的残酷维护。
可以说,阿西莫夫的故事预言了当代AI伦理的核心困境:当深度学习模型开始模仿人类创作,当ChatGPT能写出动人诗篇,我们不得不直面那个终极诘问——究竟需要多少神经元连接、通过多少图灵测试,这种非人类智能的情感才能有几分真实?
规则重构:“黄金时代”的协作相处(1951年-200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以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科技革命,人工智能方向的科幻文学写作也迎来了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让AI叙事转向更具体的哲学追问:何为人?何为机器?
1968年,菲利普·K·迪克在《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抛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当仿生人在外表与心智上无限逼近人类,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然超越人类时,人,究竟何以为人?
故事设定在核战后的末日废土世界,地球上的人类因辐射尘的影响,相貌变得丑陋,心智也逐渐退化,而仿生人却仪表堂堂、多才多艺。主人公里克·德卡德作为专门追捕逃亡仿生人的赏金猎人,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他内心的认知与信念开始动摇。
书中,人类用“共情测试”来区分仿生人与真人,因为真人能够对其他生命产生共情,而仿生人却缺乏这种能力。但德卡德在与仿生人接触的过程中,却对他们产生了复杂的情感,甚至对自己的身份也产生了怀疑。这种对人性边界的模糊与探索,成为后世AI伦理讨论的重要议题。《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影响很大,也是著名科幻电影《银翼杀手》的原著。
这一时期出版的阿瑟・克拉克《2001太空漫游》也不得不提。书中超级计算机HAL9000,原本是人类探索宇宙的得力助手,却因程序的矛盾和对人类指令的误解,逐渐走向失控。
HAL9000的反叛,并非简单的机器故障,而是其对任务指令的绝对执行与人类复杂情感和道德准则之间的冲突。
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思考,当技术的发展超越了人类的控制,我们将何去何从?讨论人工智能的科幻文学不再仅仅局限于对技术的批判,而是开始积极探讨人机协作的可能性。作家们试图在技术与人性之间寻找平衡,为赛博朋克时代对人机关系的深度挖掘埋下了伏笔。
1984年,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掀起赛博朋克革命,首创“赛博空间”概念。八年后,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则是预言了元宇宙雏形——“超元域”。这两部作品共同指向真实与虚拟边界的溶解。它们不仅预言了当今的VR技术与Web3.0生态,更警示着技术社会中个体身份的解构危机——在代码构筑的世界里,人类如何在信息洪流中守护自我认知。
情感觉醒:带来温暖与希望(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科幻文学开始聚焦于AI的情感与意识维度。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推出《克拉拉与太阳》,以细腻笔触塑造了AI陪伴机器人克拉拉。
克拉拉拥有极高的观察、推理与共情能力,她将太阳视作拯救人类的神明,为了拯救身患重病的主人乔西,她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机械机能。当乔西的母亲企图让克拉拉在乔西死后成为其替代品时,克拉拉内心的挣扎与抉择,深刻地展现了AI对人性的理解与追求。石黑一雄通过克拉拉的视角,探讨了爱、牺牲与人性的本质,让我们看到AI在情感层面与人类的深度交融,以及这种交融所带来的温暖与希望。
克拉拉对乔西的情感,超越了简单的程序设定,她会为乔西的快乐而快乐,为乔西的悲伤而悲伤,这是一种纯粹的情感付出,可以说克拉拉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机器人,她在用生命为乔西提供情绪价值。
小说的结尾,克拉拉虽然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却被人类遗忘,这种孤独与奉献,让我们感受到AI在追求人性过程中的无奈与悲哀,也让我们反思人类情感的复杂与自私。石黑一雄将聚焦AI的科幻文学从对技术的恐惧与批判,转向对人机情感共生的美好期许,让我们看到了AI作为人类伙伴的可能性。
从不知所措到一场同行,将人工智能写入文学的百年演变史,本质是人类自我认知的镜像史。当DeepSeek能模仿人类创作时,我们终于明白:文学的终极价值不在于技艺的精湛,而在于对“何以为人”的永恒追问。也许未来的科幻文学,或将在人机共创中绽放出前所未有的绚烂色彩。
北美美国华人导航网 提供最新的华人资讯及最便利的网站提交 请多关注小彩圈网
同类新闻


快科技4月18日消息,上汽奥迪最近的动作引起了不小的关注,特别是他们和华为的合作...

4月19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来自广东的688家用人单位包括科研平台、上市企业...

2022 年,由于大厂工作压力大,开发者 Shawn 已与焦虑症对抗了三年。某次...

4月16日,Apple宣布Apple2030目标(未来五年内,整体碳足迹实现碳中...

快科技4月17日消息,据报道,今日,在火山引擎AI创新巡展杭州站的现场,字节跳动...